去年秋天,父亲走后,我们一家人在骨灰安置的问题上犹豫了很久。他生前总说“别给孩子们留麻烦,找个干净的地方,让我回归自然就好”,妹妹提起海葬时,我心里其实没底——总觉得这事儿离我们很遥远,直到拨通了天津海葬服务中心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温和,问清我们的需求后,约了三天后的上午去中心面谈,末了还加了句:“如果家属多,建议带个能拿主意的人来,我们慢慢聊。”
第一次去服务中心是个周三的上午,导航把我们带到河东区的一栋临街小楼,门口没有醒目的招牌,只挂着“天津市殡葬服务中心海葬部”的木牌,推门进去时,意外地没有想象中的肃穆压抑。大厅里摆着几张浅棕色的木质桌椅,墙角的绿萝长得正好,空调吹着温吞的风,背景里有若有若无的钢琴曲。穿米白色工作服的姑娘迎上来,递过一杯温水,声音很轻:“是预约了咨询海葬的吗?”我们点点头,她引我们到靠窗的位置坐下,桌上已经放好了一本蓝色封面的册子,封面上印着“渤海湾骨灰撒海服务指南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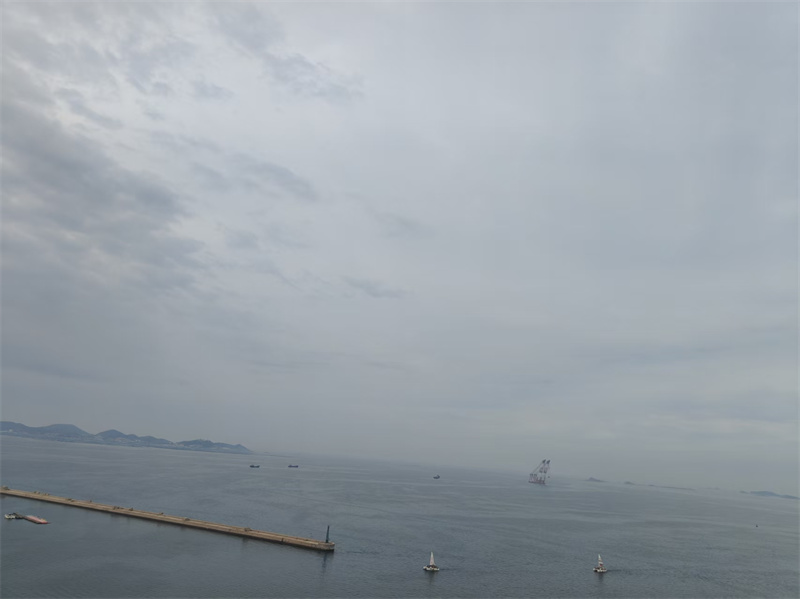
姑娘叫小周,她翻着册子给我们讲流程,从材料准备到出海时间安排,说得特别清楚。“需要逝者的死亡证明、火化证明,还有家属的身份证,这些您都带了吗?”我把材料递过去,她一页页核对,遇到不清楚的地方,会用铅笔轻轻在纸上做标记,“这个火化证明的复印件需要两份,我们这里可以复印,您坐着等会儿就好”。后来才知道,她看我母亲眼睛不太好,特意没让我们自己跑出去找复印店。中途我问起仪式的安排,她笑着说:“撒海仪式可以简单些,也可以按家属的想法加些环节。比如您父亲喜欢茉莉花,我们可以准备新鲜的花瓣一起撒下去;如果有想对他说的话,也可以在仪式上念一念,船舷边有话筒,风不会太大,他能听见的。”
出海那天是个晴天,服务中心安排的船停在塘沽港的码头。我们到的时候,小周和另外两位工作人员已经等在岸边,他们帮我们把装着父亲骨灰的盒子从布袋里取出来——那是个深棕色的陶盒,上面刻着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“海”,是小周之前帮我们联系的刻字师傅做的,说“这样撒下去的时候,也算有个念想”。仪式开始时,船已经开到渤海湾的指定海域,工作人员先撒了一把金黄的菊花瓣,然后示意我们上前。我抱着骨灰盒,母亲和妹妹站在两边,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过来,小周轻声说:“慢慢撒,别着急。”骨灰混着花瓣落入海面时,像一群白色的蝴蝶,跟着波浪慢慢散开。那一刻,我突然想起父亲年轻时带我们去海边钓鱼,他坐在礁石上,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,说“大海多好啊,包容万物”。

回来的路上,母亲靠在车窗上睡着了,眉头舒展了很多。之前总觉得海葬是“轻飘飘”的,没有实体的墓碑可以凭吊,但那天站在船上,看着骨灰融入大海,反而觉得父亲离我们很近——他变成了海风,变成了浪花,变成了我们每次去海边时,心里那点温暖的念想。天津海葬服务中心的人说,他们每年要接待上千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,“我们能做的,就是让这个告别的过程,少一点遗憾,多一点心安”。现在再想起父亲,我不再只觉得难过,更多的是感激:感激他教会我们豁达,也感激那些在服务中心遇到的人,用专业和耐心,帮我们完成了这场温柔的告别。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