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三下午,我陪母亲在老房子整理父亲的遗物。衣柜最底层的木箱里,除了他常穿的那件深蓝色中山装,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,是父亲七年前写的:“若我走了,别买墓地,把骨灰撒进大海吧。我这辈子总说想去看海,最后就留在那儿,挺好。”母亲抹着眼泪说:“你爸年轻时在工厂当技术员,一辈子省吃俭用,总说墓地太贵,不如把钱留给孙子读书。”那天起,我开始琢磨:骨灰海葬到底需要什么条件?普通人能办吗?
第二天一早,我先去了社区居委会。负责民政事务的张姐给了我一份《海葬服务指南》,又泡了杯茶慢慢说:“海葬不是随便撒的,得符合基本条件。”她拿出清单一条条划给我看:首先得有逝者的身份证明,比如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,要是没有身份证,户口本也行;然后是死亡证明,医院开的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都可以;最重要的是火化证明,必须是正规殡仪馆出具的《火化证》,上面得有殡仪馆盖章——这是确认骨灰合法性的关键。“还有家属这边,”张姐补充道,“得是逝者的直系亲属办理,比如配偶、子女,要带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,证明和逝者的关系。要是兄弟姐妹代办,还得额外开亲属关系证明。”我边记边点头,原来材料准备是第一步,缺一样都办不了。
从居委会出来,我又联系了市殡葬服务中心的海葬服务部。接电话的李老师声音很温和,她告诉我办理流程比想象中简单:先把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交到服务中心审核,审核通过后填《海葬申请登记表》,选集体海葬还是单独海葬——集体海葬一般每月一次,费用低,还有政府补贴;单独海葬可以自己选时间,但费用高些。我们选了下个月的集体海葬,李老师说需要提前预约出海时间,因为要根据潮汐和天气安排,“出海那天得早点到码头,带上骨灰盒,服务中心会提供降解骨灰坛,把骨灰换进去——普通骨灰盒大多是木质或石质的,不能直接撒,得用可降解材料,这样才环保。”她还提醒,仪式上可以带束鲜花,但不能是塑料的,也可以准备逝者生前喜欢的小物件,比如老照片、手写的卡片,“但得是能被海水降解的,比如纸质的、棉质的,金属或塑料的不行,会污染海洋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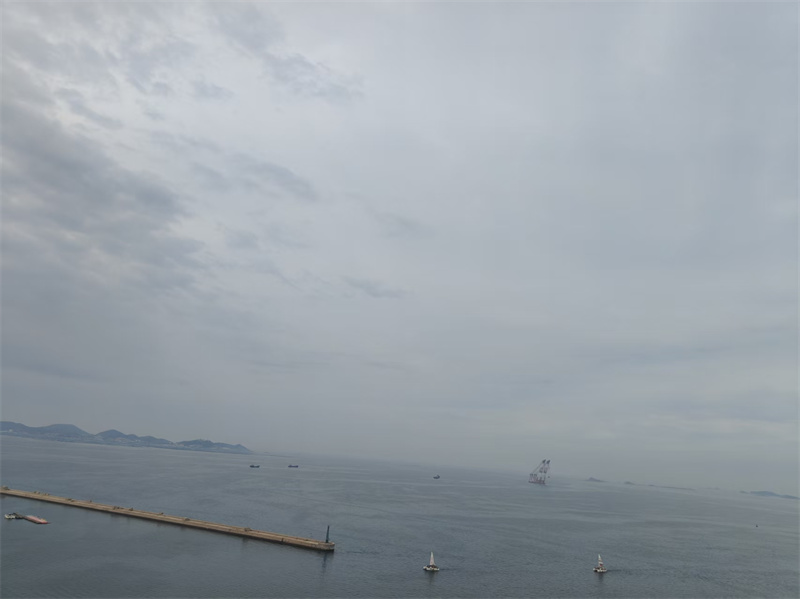
离出海还有一周时,母亲突然问我:“撒骨灰的时候,我能说几句话吗?”我赶紧打电话问李老师,她说当然可以,仪式上有家属致辞的环节,还会放哀乐,工作人员会协助撒骨灰,家属也能亲手撒一点。“不过得注意安全,船在海上会晃,老人和小孩要站在船舱中间,别靠栏杆太近。”挂了电话,我陪母亲去花店挑了束白菊,又翻出父亲生前最喜欢的那本《海洋生物图鉴》,撕下一页他画过波浪线的地方——是介绍座头鲸的段落,他总说座头鲸会唱歌,像在和大海聊天。母亲把书页折成小船的样子,说要和骨灰一起撒进海里。
昨天去服务中心领纪念证书时,碰到一对老夫妻也在办海葬手续,大爷说:“我和老伴儿早就商量好了,以后都海葬,省地方,还能‘住’一块儿。”看着证书上父亲的名字和“海葬纪念”四个字,突然觉得海葬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种开始——父亲会变成海里的浪花,变成沙滩上的贝壳,变成我们每次看海时,心里那声轻轻的“爸,我们来看你了”。原来所谓“条件”,不只是材料和流程,更是一份理解:理解逝者对自然的向往,理解生命回归的意义,理解爱从来不会被大海带走,只会随着潮汐,一次次回到我们身边。






